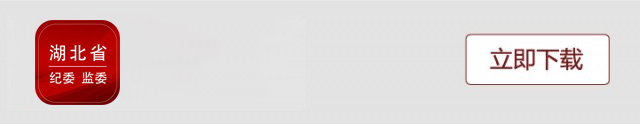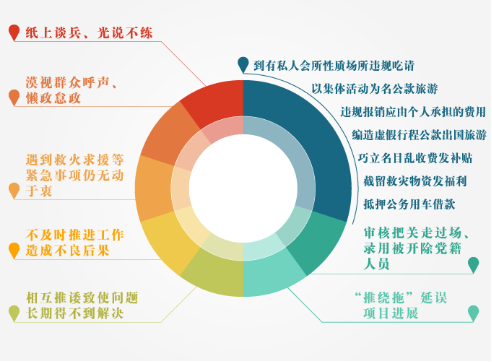赵启喜
秋天有月亮的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我和哥哥就会提上马灯,来到父亲的果园敲打板栗果。板栗树高高的,我们抄着长长的竹杆,爬上树又摇又敲的,“哗”,“嘣”,时不时有板栗果从裂开的口子掉落下来。回家后,我们用铁火钳夹起来,放在火堆中烘烤,嘭地一声,板栗炸开了,一股板栗香味飘满屋子,客人们都饱了口福,夸赞父亲经营果园有方。
记得上小学时,生产队种了一片片果园,有樱桃、柿子,板栗、核桃、枇杷……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我放学后就要远远地跑到果园旁驻足观看一番,看得我口水直流。生产队的果子不能采摘分吃,每年都要上交“公粮”,父亲就决心自己种一些果树。有一次,父亲看到自家种的一些果子上面长满杂点并发裂,就到生产队的果园里偷偷学技术,观察果树的长势,恰好被路过的一个村民看到了,大喊:“抓强盗呀”----父亲站在树下静静地说:“这些果子青青涩涩的,我怎能采摘果子吃呢?我在观察果树的长势,想学点种果树的窍门。”但这个村民一口咬定父亲在偷摘果子,告状到生产队开起批斗会,父亲成了一个“强盗”天天挨批斗。父亲也不抗辩。后来,这个村民给父亲赔礼道歉,但父亲没半点责怪,还从果园摘了一篮子果子送给他。我愤愤不平地问父亲:“为何不痛骂这个小人呢?”父亲说:“口中有德。”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父亲的果园充满诱惑。本村的、邻村的,总有小孩子放学后“光顾”果园,趁没人注意时,从角落里冒出来,扯几个果果塞到书包里,然后一溜烟跑了。父亲从田地回家后,我们就打起“小报告”。
“呵呵,树上长的果子谁都可以吃,别放在心上呀。”父亲总是宽容地一笑而过。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家中分到了一块荒山,砂砾遍地,只能生长一些杂草,在别人眼中是一块不毛之地,但父亲却如获至宝,钟爱有加,高高兴兴地打算开辟成一块果园。父亲说干就干,一有空隙就带上铁锹、斧子、镰刀到荒山上清挖岩石,砌沟垒坎,平整沟渠……一个冬天过去了,一片荒山变成了错落有致的田地。
被贫穷和饥饿折磨怕了的村民,纷纷抓住大好时机,积极寻找发家致富的门路,把目光投向自己的一亩两分地,在如何提高土地产量和多效率运用土地上琢磨。父亲带领村民种植经济作物,无私传授技术,走出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步。
父亲的果园品种较多,梨,桃,李,板栗,枇杷,枣子,柿子……一年四季,都有采摘可吃的果子,但果园里数量最大的还是板栗树。在我记忆中,初夏板栗树开花,很细小,丛集在花枝上,成条形,每条约六七寸长,十几条花枝集栖在一起,成为一簇簇。一棵板栗树,缀着成百上千簇,甚为壮观。远远看来,绿妆玉饰,虽没有姹紫嫣红的艳丽,但素妆淡雅,不鲜,不艳,却张扬,别有一番风韵。秋天,果实丰满,绿色鼓胀的刺球密密地将整棵树包围着,成熟的栗果裂开了,露出乌红闪亮的板栗,像玛瑙,像仙丹,栗蕊飘香,沁人心脾,引来行人驻足观赏。
父亲成了板栗栽培“专家”,品种较多,有早有迟,有大有小,有香有甜。果园中有两棵 “栗树王”,特别高大。一棵是羊毛栗,球大剌长,结的一个板栗相当于普通板栗的两三倍重。这种板栗,乌红的壳上长着一层白色的绒毛,握在手上感觉很舒服,剥开咬栗肉,又脆又香,让你反复咀嚼,舍不得咽下。另一棵叫“九月寒”,比一般板栗成熟足足要迟两个月。打霜的季节,别的栗树叶都落尽了,它才成熟,果实中等个头,但是香甜无比,口感特好。
板栗收回后,父亲就会将这些板栗铺到楼上的阳台,吸收夜间的露水,用父亲的话说叫“露板栗”,白天又收回家,摊铺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如此反复几昼夜,板栗就甜了。父亲就将这些收获,一一送给乡邻们品尝。
俗话说:桃三杏四梨五年。父亲的果园历经风霜雨雪,一天比一天富实而沉甸,成了我们的的乐园,鸟儿的天堂。这几年来,每当我假期回去,总会见一些有果树种植经验的爷爷或者大伯到我家喝口茶,去果园看看。听着大家的溢美之词和父亲面容上舒展开来的皱纹,我和母亲默默地在心中为他鼓掌,父亲和他的果园已然成为我们一家人的荣耀。
生活的艰辛磨不平世事的坎坷,风雨流离之中,我渐渐看清楚生活的面孔,它是父亲额上的沟壑,它承载着父亲的果园与希望,散发着父亲手捧的果香,折射出父亲的人生信念:口中有德,心中有爱,行中有善。(作者单位:点军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