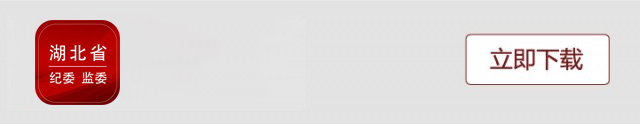2020年9月10日至11月15日,“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该展通过三大主题、18个历史节点介绍紫禁城的规划、布局、建筑、宫廷生活,以及建筑营缮与保护的概况。图为游客参观紫禁城宫殿建筑全景模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为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专家指导修缮技艺部修复承乾宫天花。(《我在故宫六百年》制作团队供图)
故宫跨年,一跨就是“六百年”。
从2020年12月31日到2021年1月2日,纪念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的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晚间黄金档与观众如约见面。
现象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播出后风靡全网,故宫专家修复故宫文物的故事打动无数人,更掀起了对文物修复的关注热潮。作为姊妹篇,《我在故宫六百年》依旧聚焦故宫里的人和物。这一次,主角是古建筑,还有故宫古建的守护人。
故宫古建承载厚重历史,解读紫禁城砖瓦梁木间的文明密码
随着午门缓缓打开,《我在故宫六百年》的故事拉开大幕。
从紫禁城落成到今天,昔日的紫禁城已成为故宫博物院,跨入了第601个年头,至今仍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
“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多数博物馆相比,除了具有丰富的藏品外,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建筑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馆藏’,而古建保护传承对故宫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我在故宫六百年》导演之一梁君健告诉记者,如果说《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的是钟表、瓷器、书画等可移动文物,那么《我在故宫六百年》关注的是故宫不可移动文物——古建筑。
故宫时间跨度大、古建数量多,故事如何讲述?《我在故宫六百年》从一场耳熟能详的展览说起。
东华门内,设立于1958年12月的故宫博物院古建部负责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2020年春天,他们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策划筹备一场名为“丹宸永固”的展览。
丹,是宫墙的红色;宸,为深邃的宫殿。六百年来,紫禁城曾见证无数风云变幻,如今,它也成为历史本身。展览讲述的,是有关紫禁城建筑规划、肇建、变迁、修缮与保护的种种往事,而纪录片记录了策展过程中,故宫人探寻紫禁城古建前世今生的独特经历。
追根溯源。为探寻紫禁城最初的模样,摄制团队没有局限于故宫四方红墙内,而是跟随策展团队奔赴千里之外的安徽凤阳寻找答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初想把皇城建在家乡,却在六年后意外叫停,凤阳的中都皇城成了一座皇家“烂尾楼”,却保留了紫禁城“土作”工艺的秘密,由此揭示了“丹宸”得以“永固”的根本原因。
见微知著。在午门展厅,一片蓝色瓷砖赫然出现在“丹宸永固”大展上,在453件展品中似乎毫不起眼。事实上,它身世神秘,来自遥远的德国,是灵沼轩遗留下来的建筑材料,见证了紫禁城作为皇宫的最后余晖。100多年前,这些印有精美花纹的瓷砖漂洋过海,涂装在这座故宫唯一的西洋水殿中,意外地成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传承古今。养心殿正殿后檐雨搭上的明瓦屋顶,或是北京仅存的一处“贝壳屋顶”。屋顶瓦片由大而平的海月贝壳制成,如珍珠般玲珑剔透,展现着古人的工匠技艺和生活智慧。在展览筹备过程中,为展示这些明瓦的功能和沿革,当代故宫保护者前往苏州拙政园和广东沿海地区,为明瓦的修复寻找材料……
“围绕故宫古建筑的历史、保护和展览,我们既讲述故宫六百年的历史沿革,展现紫禁城承载的无限时空,也挖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老、中、青古建保护者们代代相传的独特故事。”梁君健介绍,《我在故宫六百年》以“丹宸永固”大展、养心殿大修工程、岁修保养等为线索,通过故宫古建部、工程管理处、修缮技艺部、文保科技部、考古部等部门的工作视角,开启故宫“再发现”之旅。
“这些‘新发现’既有故宫深处的大历史,也有故宫古建中的趣闻故事,更有紫禁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间的文明密码。”梁君健说。
细腻呈现故宫古建修缮过程和技术,跨越时空寻找岁月印记
“等了四年多,终于等到你!”“期待已久,跨年最大惊喜来了!”新年第一天,在以年轻用户为主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我在故宫六百年》第1集《“丹宸永固”的秘密》播放量接近70万,吸引了大量观众参与弹幕评论。
作为口碑佳作《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我在故宫六百年》播出前就“自带流量”。据了解,此次创作团队基本是原班人马,镜头语言、影片风格也一脉相承。
据悉,《我在故宫六百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摄制,内容制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创作团队和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创作中,梁君健担任策划和撰稿人,而他与故宫的缘分则更早,2010年时就和其他纪录片团队成员一起深入故宫博物院做调研,撰写了数万字的调研报告,为后来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拍摄一部故宫古建修缮保护纪录片的想法,早在4年多前就萌生了。”梁君健说,《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结束后,团队成员们聚在一起聊天,想拍古建这个“大文物”的想法不谋而合。
古建修缮门槛高,专业性强,相应地也给拍摄者带来挑战;拍什么、怎么拍,以及如何跟上故宫古建保护专家们的“节奏”,成了创作团队的“必修课”。
2020年5月开机,不久因疫情影响暂停,再次开机就到了7月下旬,直到片子播出前,12月还在补拍镜头。“故宫不是一天修好的”,能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一部讲好故宫故事的纪录片,背后是团队的长期沉淀和留心学习。
“在古建部拍摄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老师的办公桌上有两本书,分别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和《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这两本都是八九十年代的书,我找到后放在手边,经常翻阅,拍摄、采访过程中遇到问题也会去书里找答案,这样采访沟通的时候能听得更明白、聊得也更深入。”梁君健说。
时空,是《我在故宫六百年》的一条内在线索。光阴流转、世事变迁,紫禁城带着历史的记忆,凝聚成故宫这一文化符号。“我们想要讲述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这次故宫六百年大展的策展思路是以时间轴展开的,而《我在故宫六百年》想讲述的,同样离不开紫禁城六百年的时光。”梁君健说,纪录片从古建筑出发,探秘紫禁城最初的模样,也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等中探寻古建的生命脉络与那些惊心动魄的跌宕起伏,还有“隐秘角落”里不为人知的趣事,“这部片子带我们重新认识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宫。”
不局限于一城一池,六百年间有着广阔的空间线索。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是开放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客厅,而古往今来的紫禁城,也一直是一个承装天下万物的容器,世间的精彩皆汇集于此处。
“我们拍到在修养心殿的过程中,屋顶一些砖瓦坏掉了,而新换的琉璃瓦是在山西烧制的;一根扶脊木糟朽了,替代它的木头来自东北,经由天津的木材市场连夜运进故宫。”梁君健告诉记者,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宫墙之内有悉心呵护故宫的匠人,宫墙之外的天下人也与这座城池发生奇妙的关联。”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丹宸永固皆因代代故宫人薪火相传
“瓦木石扎土,油漆彩画糊”,俗称“八大作”,是紫禁城营造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木作可以说是营缮中最重要的主作,木匠更有“百艺之首”的美誉。
拍故宫角楼,是不少摄影爱好者的“心头好”;修过角楼,则是木匠可以回味一辈子的荣耀。
夏荣祥,1975年进入故宫,2017年退休,在这里度过了42个春秋。作为故宫的第三代大木匠,他先后参与了两座角楼的修缮。“丹宸永固”大展在即,古建部的狄雅静请夏荣祥过来指导展品设计。
1981年,夏荣祥跟着年富力强的师傅们参与修缮了东南角楼;1985年修缮西南角楼的时候,夏荣祥自己也成长为掌线师傅。
开展前,夏荣祥来到午门展厅,大木匠的传统工具已经按照他的建议制作完成。在展厅,夏荣祥走到一张1957年故宫西北角楼大木修缮工程竣工,匠人和专家们在工地的合影留念前。夏荣祥的师傅们就在合影之列。值得一提的是,照片右边还有一张轮廓图,上面写着照片中修缮者们的姓名。
六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而对于建筑和建筑的守护者而言,却意味着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沧桑更迭。在《我在故宫六百年》里,表面是讲建筑、讲营造、讲修缮,归根结底还是在讲人的故事。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我们希望能体现当下正在发生的人和事,探讨人和建筑的关系。”该片另一位导演张越佳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关注故宫的恢弘建筑,关注流光溢彩的珍贵文物,但对它们的建造者、守护者知之甚少。“《我在故宫六百年》里,他们是主角。”
杨红是故宫古建部的中坚力量,从她的师父王仲杰老先生那里系统地研习明清官式建筑的“油作”和“彩画作”的传统知识。这几年,她一直在从事故宫彩画的画样复制,虽然师父已经退休,但遇到难题,她还不时地去拜访和求教。
王仲杰老先生是“古建彩画”领域的泰斗级人物,86岁高龄仍执著于彩画保护和创作。“老先生给我印象很深,退休后那么长时间,他每天在家一有空,就自己拿起笔去画彩画,做研究,他还给我们展示过一个3米多的卷轴,想把北京中轴线主要建筑上有代表性的彩画复原在这样一个卷轴上。”
退休后,夏荣祥也没闲着,一直专注于给年轻的故宫人讲授匠作课程,古老的技艺得以代代延续传承。
张越佳说,影片所要呈现的正是许多像王仲杰、夏荣祥一样的故宫守护者,如何用妙手与巧思、智慧与心血来延续这片古老建筑群的无价生命。
历史文物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我在故宫六百年——“我”是谁?
这是不少观众看到片名后的疑问,也是创作者拍摄时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是在紫禁城伫立六百年的建筑。故宫是当代中国人对于自我身份和共同历史的重要认同符号,故宫的古建筑则是紫禁城的时间机器,一砖一瓦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戏曲是清代紫禁城重要的娱乐项目,逢年过节少不了它。“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中,工作人员清理养心殿的一块透风砖时,居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近200年前的戏折,是清代的‘跨年演出节目单’。”梁君健说,这份穿梭时光而来的意外礼物,它的主人是谁,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当时演出的气氛怎么样,留给了我们无限的研究和想象空间。
“我”,是悉心呵护故宫的匠人和学者。六百年来,这里遭遇过雷击、焚毁、糟朽等数之不尽的大病小灾,但一代代工匠、学者在漫长的接力中付出时间与责任,一次次“妙手回春”,留下了红墙黄瓦,流光溢彩,更留下了可以再说六百年的紫禁城。
宫墙之外,天下人也是故宫的见证者、参与者和爱护者。“今天人们对古老故宫的爱,是大家更愿意围绕故宫创作的直接动力。”《我在故宫六百年》撰稿人司徒格子告诉记者,近几年故宫变得越来越“年轻”,从一个严肃的文化形象变得让人可亲可近。“游客模样也悄然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穿上清宫戏里的衣服来拍照、录视频。这些变化都是深爱故宫的人推动出来的。”
纪东歌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从事瓷器修复工作,因《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为观众熟知,这次在《我在故宫六百年》,许多观众一眼认出她,直呼“亲切”“惊喜”。
纪录片也为故宫带来活力与改变。“片子播出后,好多年轻人羡慕我们,非要学这个。”纪东歌一边清洁着手中的蓝色瓷片,一边说道,“但光学这个清洁材料可能都要学一年。”
如今,文保科技部从几座小院搬进了位于故宫西侧院墙内的文物医院,在采用传统工艺保养修复文物的同时,文物医院也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吸引更多年轻力量投身文保事业,共同守护故宫的“健康”。
每当夕阳西下,从北京景山公园的万春亭鸟瞰,故宫红垣溢彩、黄瓦流光,大气磅礴尽展眼前。如今,故宫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无论是春暖花开、寒冬雪落,还是新上了专题展或文创品,都有很多人专程去“打卡”。
物的延续和人的传承,让故宫留存至今,也让每一个身处当下的人在这片古老的建筑中获得力量和信念,伴随故宫从悠远的历史走向生生不息的未来。